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评奖揭晓、颁奖后
其书法创作类获奖作品
在书坛引发热议
为此
《书法报》特邀
王登科、张瑞田、周德聪、
杨吉平、庆旭
从不同角度对获奖作品
开展学术评论
至本期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获奖作品
批评系列刊载完毕
感谢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支持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获奖作品集评·樊利杰

樊利杰 1975年3月出生于河南郑州,现居武汉。湖北省书协副主席、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书协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作品获第六、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铜奖、第三届获奖提名,第六届湖北书法黄鹤奖一等奖,湖北省第十一届“屈原文艺奖”等,荣获“兰亭七子”“湖北省最美文艺志愿者”“湖北书法突出贡献奖”等称号。入展第九、十、十二届国展,以及青年展、小品展、楹联展、册页展、草书展、行书展、扇面展、新人展等中国书协主办的展览30余次。获2021年湖北省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中国文联2020携手铸梦扶持项目。发表文章约60万字。
王登科(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委员、荣宝斋书法院院长):
樊利杰作品(图1—图3)的主要基调是董其昌。其清雅、温婉处,正可谓“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时下书坛,竞赛工巧,因此,大多书家取法也都“人云亦云”,并呈现“扎堆”的特点。樊利杰能够择此“僻境”,而且一如既往,这确实难能可贵。
中国文化重“天人合一”,主张“格物”,君子人格的“生命内省”即是其中的延展。绘画中的“荒寒”、诗词中的“平淡”皆如此。这一点恐怕是利杰在书写中的会心处。
当然,不管是董其昌也好,还是“疏淡”也罢,这些都是我们走进传统的一些启示。重要的是,我们要走回自己的内心,去道出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是所谓的“传统”。
真正的“传统”不在过去,它,在当下,在我们的心底。以此,并与利杰互勉。
以上,应《书法报》之约,对诸友的大作,一一赏读,受益匪浅。赞叹之余,也有疑窦相与析,或是“为赋新词”之想,并不揣谫陋,姑妄言之,并请诸友海涵,也以此就教于方家。

图1 樊利杰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铜奖作品
行书自作文《母亲的心愿》中堂

局部
张瑞田(中国书协新闻出版传媒委员会委员):
樊利杰的《董其昌书风的当代观照》一文从大处着眼,对董其昌书法的文化历程进行梳理,从中可以窥见他对董其昌的理解,对学习董其昌书法的切肤感受。他说:“随着整个社会对传统认识的逐渐加深,研究和学习更加关注书法本体,董其昌书风在当代渐渐走出了上代人的囿识,特别是随着帖学的再度兴起,对董其昌的认识也愈加客观理性,这也促进了更多人来关注董其昌、学习董其昌。”
樊利杰讲出了董其昌书法的当代处境,也讲出了为什么学习董其昌书法的理由。这篇文章,是研读樊利杰书法的重要文本。就像作家所写的创作谈,它阐释了作家写作的动因和追求,为读者和观众的阅读提供了参考的依据。
放下樊利杰的《董其昌书风的当代观照》,再看他的书法,就会若有所思。
樊利杰在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中获铜奖的三件作品,与他此前的作品没有本质的区别。看着这三件作品,想到他研习董其昌书法的心得:“要让书法作品有韵味,手头就要留有余地,能连的地方不急于连,可倾斜的地方不急于倾斜,用淡雅的心态去面对这些纸和墨。”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樊利杰书法的特点离不开“能连的地方不急于连,可倾斜的地方不急于倾斜”,很像书斋中的书写,一边思考,一边挥毫,把心事留在纸上。这样的书写是樊利杰的选择,也是他追求的美学情趣。他看似轻描淡写地说“用淡雅的心态去面对这些纸和墨”,其实,这里面包含了他对传统书法的理解,对当代书法创作的体悟。
“文书一体”,是三件获奖书法作品的共同特点。其中一件书录的是自己散文。我逐行逐句阅读行书《母亲的心愿》,文章有深情,书写有人生况味,读起来可以与樊利杰的内心发生共振。对于当代书法创作取材白话文的行为,我是支持的。我的理由很简单,当代语文以白话文为主,当代书法不应该回避对白话文的书写,反而要加大力度探索白话文书法的创作方法和实践规律。看到樊利杰行书《母亲的心愿》,我觉得白话文书法大有前途,这不仅拓展了当代书法的创作方法,也将提升当代书法的美学品质。传统书法主要书写韵语律诗,这是对彼时官方语言的遵守,是中国书法完整而协调的文化体现。当文言文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白话文成为全社会主要使用的语言工具,我们就要正视白话文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延伸和影响。因此,樊利杰的行书《母亲的心愿》就有了另外的意义。
作为书法作品的《母亲的心愿》,依然可以看到樊利杰书写时的小心翼翼,这一点可以理解。毕竟不是原始的文稿,而是参与当下一次重要的书法竞技式评奖。在尊重文本的同时,作者考虑到书法作品的书写规律,“强调书写性,一画与一画之间、一字与一字之间、一行与一行之间的关系,都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气息弥漫。书写的时候,由笔顺产生笔势,再由势产生气,由气而生韵”(樊利杰语),因而有了主观书写与客观书写的呼应。樊利杰把董其昌视为重要的书法资源,把在思考、临写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价值、所积累的经验,成功转换到他的书法创作实践。因此,我们在樊利杰书法创作的总体框架中,对董其昌有了重新发现,对樊利杰书法的文人趣味有了清晰的印象。
“学习董其昌,既要了解董其昌的身外世界,更要细心感受他的精神世界、思想境界,体会他笔下的由来。”我对这句话很有感觉,当代书法家仅仅知道一位经典书法家的身外世界是不够的,深邃的精神世界、高度的思想境界,更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鹄的。

图2 樊利杰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铜奖作品
行书自作《游学诗四首》横幅
周德聪(中国书协书法教育委员会委员、三峡大学书法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第七届兰亭奖所有的创作类获奖作者中,只有樊利杰创作的三件书法作品,其诗文皆是自撰。仅此一点,就拉开了与“展览体”“文抄公”的距离。
当代书法由复兴走向繁荣,经历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无论是传统与现代之争,还是技法与艺道之论,都在书写的实践中渐渐趋向共识——向传统回归,致敬经典,弘扬书法道统;向未来奔去,写出个性,彰显时代书风。既要艺文兼备,更需德艺双馨。
在近些年中国书协举办的展览、评奖的征稿启事中,“提倡自撰诗文”似为常规,而在本届“兰亭奖”的征稿中,则将“提倡”变为“必须”了,即三件参评作品至少有一件作品为自撰诗文,这在第七届兰亭奖评奖中落实得十分到位。
樊利杰参评的三件作品,一件为散文《母亲的心愿》,长达1400余字。另两件为《观画诗》(五律)及《游学诗四首》(七绝一首、五律一首、七律两首)。他没有展示书擅多体的能力,而是以其最为擅长的行草创作了三件不同幅式、不同意象的作品。
《母亲的心愿》以记事的方式,表达作者对母亲的“爱”,在一件件看似平实的事件中,既表现了母亲的平凡与伟大,也表达了作者的慧心与情感。他用相对稳健的行书,以三个条屏连缀成一个整体,写来从容不迫,于波澜不惊中将文情与书意作了“静水流深”式的诠释及演绎。
他的书法,属典型的帖学一派,上溯晋唐,中法宋元,下探明清,于董玄宰用功尤勤,追求古淡清丽的书风,在当代书坛独标一格,并被专家学人认可,其连续两届获兰亭奖铜奖即是明证。
学习书法,有遍习诸家而后融通者,有笃守一家作深入开掘者,樊利杰无疑属于后者。他多年来潜心于董其昌行草,以此为根基,既溯其源,亦探其流,故能在表现董其昌之清、淡、古、雅的同时,也不乏对拙、厚、娟、朴的眷顾。写一首诗或数首诗,百字左右,可以反复试错,直至满意为止。而一篇千字以上长文,单是抄录也要几个小时,更何况在书法的创作中,既要留意于文的准确,也要展示其技艺的多维表达与风格的一致性,还要兼顾形式的完备,非有定力、慧心、静气是不能完成的!
从艺术的审美角度对此作进行深入的体察,我们也依稀感到平实有余而起伏不够,文章的情感与书意的表达之间,既可有其一致性,也可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非常性”。恭谨地抄录与过于均匀的分布,可能会削减“艺术”带给我们的“惊喜”。
他的另外两件作品,一为《观画诗》中堂,一为《游学诗四首》横幅。
前者为利杰近年来最为常态的书写,他将董香光疏朗的字距与行距用于大幅作品的创作之上,并无松散之弊,而且通过点画的呼应、线条的长短、墨色的变化以及结字构形的大小、奇正、纵敛、疏密,使整体章法富于动感,达于和谐,笔势之“动”与气韵之“静”相辅相成,简净之中有一种素朴的大美。他的用笔总体上呈现一种收敛之势,结字亦以紧结为主,但几处放笔所显现的潇洒,既见“逸兴遄飞”,又呈现理性克制,可谓恰到好处。
而行书《游学诗四首》,以横卷的幅式来表现,有卷舒自如之态。中锋行笔圆劲流丽,线质简净,墨色浓淡枯润相间。表现出一派清和气韵,虽是草书却悠然行笔,不激不厉,自有其风规。他尤其重视墨法,无论轻重粗细还是快慢疾涩,都写出墨色的层次感,而层次无论怎样风云变幻,皆绝去枯燥浊陋、鼓努为力,而存清亮通透、圆活华滋。
历史上从二王帖学中走出的书家,俱有得失,然必以某种发现而留名书史,如李煜《评书》所云:虞世南得其“美韵”,欧阳询得其“力”,褚遂良得其“意”,薛稷得其“清”,颜真卿得其“筋”,柳公权得其“骨”,徐浩得其“肉”,李邕得其“气”,张旭得其“法”……他们都在有所得与有所失中前行。今人草书,尽管可以一窥先贤所有经典,但不可能将其众长汇于笔端(当然我们满怀理想地期望如此),只能在历代经典法帖的研习中,结合自己的心性,在某一方面有新的发现与开掘,从而丰富当代书法探索的语境,这对于年轻的利杰,或是有担当的书家,都是值得期许的。当下兰亭奖评委对樊利杰书法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书法回归传统)上是对董其昌书法风格的礼赞,因其笔下有非常纯正的“董其昌意味”。
当我们能清晰地指认樊利杰的书法是董其昌书风中“这一个”,而非“芸芸众生”相,也就离成为真正意义上具有自家面貌的书家不远了。

图3 樊利杰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铜奖作品
行书自作诗《观画》中堂
杨吉平(山西师范大学书法学院副院长兼书法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如果是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的书法,那还有可能是偏见,如果是十个人不喜欢一个人的书法,那就可能是这个书法家的问题了。董其昌书法笔者由始至终都不大喜欢,而且后来发现不喜欢董其昌书法的人远不止笔者一人。
傅山这样评价董其昌书法:“晋自晋,六朝自六朝,唐自唐,宋自宋,元自元,好好笔法,近来被一家写坏;晋不晋,六朝不六朝,唐不唐,宋元不宋元,尚煗煗姝姝,自以为集大成,有眼者一见,便窥见室家之好。”康有为则评价董其昌书法:“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以之代统,仅能如晋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旧物而已。”“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军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沙孟海评曰:“他(董其昌)的字是远法李邕、近学米芾的。明末书家,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锺并称。他的造就,本也了不异人。可是他后运好,他的作品为清康熙帝所酷爱,一时臣下,如蓬从风。自来评董字的,大抵言过其实。梁巘说他‘晚年临唐碑大佳,然大碑版笔力怯弱’。这话比较公允些。”这三位都是古今公认的书法大家,所说自然绝非信口开河。
一流书法首先应具有一流的气象,也就是大家气象,而非寒俭拘谨的小家子做派。董其昌显然属于后者。前些年上海博物馆曾举办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笔者曾亲往观看,观看的结果更坚定了笔者的看法。古人所谓“书如其人”,诚不欺人。这也就意味着董其昌的书法并非当代书家取法的首选。然在过分讲究追求个性的当下,猎奇好异、取法冷僻则成为许多书法人的一种选择,樊利杰先生正是作出这种选择的书法人之一。
笔者相信,樊利杰选择学习董其昌不一定意味着他最看重董其昌,而是选择董其昌便避免了举国皆学二王造成的千人一面的弊端。然而,不学二王便意味着取法乎下,学董其昌便意味着取法乎下。樊利杰先生的三幅作品均为董其昌风格,故其作品便具有董其昌书法的不足。首先是中气不足。傅山先生言书法首重中气,中气足则生命力旺盛,下笔便生龙活虎,气象感人。樊利杰的作品笔画瘦削,又多出以侧锋;无论是其行书还是其行草书,多为字字孤立,互不联属;其作品用墨也以淡墨为主,缺乏浓墨的醒目与豁达感。从整个字势来看,笔画收敛,字字皆向内收缩,拘束之态难掩。而董其昌严谨的结构樊利杰却没能完全掌握。其作品不时出现结构失势的字(如行书自作诗《观画》中堂中的“路”“家”等字),暴露出其楷书功底的不足。

图3
樊利杰作品的长处是整体章法和谐统一。三件作品中,章法最好的是草书横幅,其次是行草中堂。草书横幅一气呵成,首尾连贯,线条轻重变化也较为丰富,墨色整体上虽然偏淡,但浓淡还是有较为明显的交替变化,这些无疑都丰富其作品的表现力。中堂作品字字独立,看似散漫,实则用意。此次获奖,应该说章法的成功给樊利杰的作品加分颇多。
从取法上说,虽然樊利杰与崔寒柏都属于取法乎下的情况,且都是为了避熟就生、避免雷同,但其取法还是比崔寒柏要高些,毕竟董其昌是自成一格的大家。问题是樊利杰对董其昌的理解也还是不够到位,与董其昌原作相比,其笔力的厚度所差距离尚远。诚所谓屋下架屋,仅仅在董其昌作品中兜圈子,要达到董氏的水平尚且不够,遑谈超越了。所以,樊利杰先生必须突破董其昌,向书法的最高境界——晋韵迈进。帖学书风离开了王羲之,便是取法乎下,是很难达到书法的高境界的。

图2 局部
庆旭(苏州市书协副秘书长):
无需对樊利杰的书法历程作完全梳理,只要看笔性就知道他也是从二王而来的,这几乎可以看作是常识。
书法界学二王者应不止十万人,据不完全统计,仅苏州(包括昆山、常熟等县级市)一地学习二王书风的各类书友就有一万人左右。目前苏州的中国书协会员有200多人、省级书协会员有1000多人、市级书协会员有1500多人、区级书协会员有2000多人,所谓“有证的”就将近5000人(这种统计是各级会员不重叠)。另外,还有社会各界的书法爱好者,虽然数据不详,但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而苏州书法中人几乎没有不学二王的,这样看来,一万人左右的数据绝非子虚乌有。现在全国那么多“书法名城”“书法名乡(镇)”甚至“书法村”,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书法社区”等,这些都为书法发展提供了层次丰富的支持。学习二王的人还会越多。在数以万计、十几万计、几十万计的王系大军中能让人记住自家面目何其难哉!于是,大家都在实验、调整、变革……樊利杰对董其昌书风的选择,并阶段性地定格,应该说是成功的。
谈论元明书法,书道中人常将“赵(孟頫)、董(其昌)”并列,钩沉二者在帖派上的历史意义。细究二者的书作,其差别虽不可用“迥异”而论,内质还是有显著的不同,当然这是董在避开赵。但二者对古典的师承却有半数以上的交集:赵孟頫由宋高宗赵构入手,后取法王羲之、王献之、王僧虔、智永、褚遂良、李邕、陆柬之、徐浩、张旭、颜真卿、柳公权等;董其昌由虞世南、颜真卿入手,后取法锺繇、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李邕、怀素、杨凝式、米芾、苏轼等。虽有重合,但二人对古典的取法方式和开拓性却截然不同。我们可从董其昌对赵孟頫书法的评价中看出蛛丝马迹:“余书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文敏之书,病在无势,所学右军,犹在形骸之外。右军雄秀之气,文敏无得焉,何能接武山阴也?”(《容台别集》卷二)
这两段评价,虽说是各有短长,显然是在扬己抑赵,尤其第二段更是直接指出赵孟頫在“势”与“雄”方面的不足——也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以历史的、全面的眼光观之,赵、董二人在二王系书风的继承上皆作出杰出贡献。董其昌晚年曾表示年轻时对赵书的认识有偏激:“余年十八岁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三希堂法帖》卷四)笔者以为,董其昌在二王系笔法多样性、笔意丰富性、笔势深邃性及长线美学风格实验、淡雅墨法开拓、萧散意境营造等方面技高一筹。樊利杰在这几个方面可谓得其三昧。
然而,晋代以后二王系书家各类分支风格中,名派面目独有千秋,董其昌的标志点太多了,如何突围,这是取法董派书风作者必需解决的课题。有一类看似省心省力者,即直接从董帖中搬元素,未尝不可,但据我有限的知识积累,我还是认为要尊崇“取法乎上,得乎中”的道理。所以,写好董其昌必先有《集王圣教序》的功底,再有米芾《蜀素帖》的贯气意识。前者是“立骨”,能使所有线条站起来。写董其昌最要避免的是“软骨”。“虽然《画禅室随笔》中多有对米芾的推许,但其总体格局则仍然是上承二王一路。在当时,王羲之仍然是正宗。但是很遗憾:魏晋风度的潇洒意趣在历经唐宋元明诸家陶冶之后,在董其昌手中变得越来越‘女性化’,娟秀有余而雄强不足。作为技巧上的大家和风格上的庸人,董其昌是个十分矛盾的典型,他的文人理想使他连祝枝山的粗率也不敢问津。”陈振濂先生对董其昌书法的“女性化”之论,从一个侧面道出董书的风格特征——“秀”得过于阴柔。在樊利杰作品中没有见到过于阴柔的秀,这显然得力于此前他对王羲之骨力与风神的实践与把握,从他15年前的行草作品便可知。按理说他也可以沿着羲献继续走下去,说不准也是另外一个行家里手。但个体的选择既是每个人的自由,也仿佛有艺术生涯冥冥之中某种前世的约定。
樊利杰本届“兰亭奖”获奖的三幅作品皆有可圈可点处,我以为手卷最为精彩,中堂大行书次之,直幅自作文小行书再次之。在纯以董其昌风格为载体的创变中,三幅作品最可贵之处在于对同一种风格内部系统美学元素的细致深挖。他的书写实践很有点像理论类的博士论文,以一个专题把需要解剖的点分析得玲珑剔透。对于在临帖或创作过程中浅尝辄止、深入不下去的诸多书友来说,深入研究樊利杰董系书风的成长过程定有事半功倍的借鉴效应。他的这幅手卷作品几乎可以代表目前他的董系风格的最高水准,在当今书坛写董的作者中,这幅作品应该也有一定的当代意义。在更多还未离开“董形”技术修炼的作品中,这幅手卷已自如地表现书写者在精神层面的思考了。在董其昌略有重复的笔法形式上,樊利杰似有更多手段,譬如适当的铺毫除了增加线条的厚度外,与其后松弛散淡却隐含着丝丝入扣的细圆线的线条形质相互交织,给整幅作品在线条形式上增加了无限的感染力。不可否认,这幅手卷的长线连带和淡墨运用的神理显然得到董其昌《试笔帖》的某些启示,过渡得非常成功。
相较于手卷的前后顺气、通篇浑融,其中堂大行书注重的是个体观照。与通过加入碑意放大书写王羲之的书法同道所不同的是,樊利杰放大书写董其昌没有加入更多辅料,而依然立足于董其昌标志性的书写方式。他的着意点在于“笔势”的多向延展、线条疏密布局的大反差及个体结构欹侧涵义的恰当演绎。书写的精神状态应是相当松弛的。不然,此类独立型风格十有八九会令人观之呆若木鸡。因为文字较多,而且是自作文,所以,直幅小行书那幅写得随意有余、法意不足。感觉总是在重复着简单而固定的招数,感染力也弱化了不少。乍一看,像是硬笔书法。所以我认为此作应排在第三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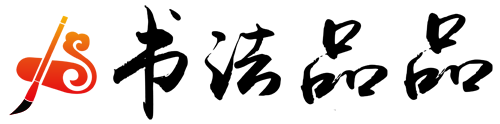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