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7年,这是让所有中国人耿耿于怀的年度,7月,北京和天津相继失守,11月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失守。侵略者显示了所有的屠杀技能,让中国人经历了空前的灾难,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何以东瀛这样的弹丸之国,竟可以到这里大肆砍杀,这是让我们不能不永远警惕了。
同年同月的乌江镇,飞机大肆轰炸,到处是炸弹爆炸的惨剧。慌张归家的林散之躲在江家棉花行,一颗二尺长的炸弹穿过房顶,落在厅堂。闭眼等死的林老并没有听到爆炸的声音——鬼子的炸弹也有臭子。逃回江上草堂的家中,才有了大难不死的侥幸,这年林老四十岁。
江上草堂——这是个多么浪漫的名字啊!
三十二年后的冬季,战争气氛由于国防部长的一号命令,骤然紧张。尽管这一年的元旦前夕,第三颗氢弹爆炸成功,南京长江大桥全线通车,再到我们这里乱杀乱砍我们就不客气了,然而,国民还是相信,侵略者一定会变着花样的。对于战争会随时威胁我们,国人深信不疑。
林老以七十二岁高龄被疏散,回到久违了的江上草堂。
“云是备战争,老弱齐迁避”,林老被迫再次回到江上草堂,他曾经意外地躲过了炸弹爆炸的地方。“地随江北冷,人自江南瘦”,归来的林老,会不会想起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呢!不得而知。然则,诗句“风雪今归来,山中茅屋漏”,也着实与“小屋如泥舟……破灶烧湿苇”的情景相似。
意外地躲过炸弹,也意外地经历了生死之劫。其时已经是1970年的2月,农历则是春节前夕,林老到乌江镇洗澡。是否经过了棉花行,是否想起了那颗没有爆炸的炸弹使得他逃过了劫难,事无记载。气雾弥漫,林老跌入滚水锅中,被人救起,血肉模糊……写到这里,让人很是难受。往下再写,心情已经惶然,揪心以至空旷。没有必要做详尽的叙述,那样会很残忍。林昌庚先生所著《林散之》一书,为记录那段历史,有真切的描述。
这意外是太意外了。林老居然活了过来,还奇迹般地将主要执笔的拇指食指中指分开,然则,“劫后归来身半残”,无名指和小指粘连在一起,并且向内勾着,则无可再恢复了。
林老自幼灾难重重,幼年就左耳失聪。听到的声音比别人少比别人小,又天性顽皮,状异恒人,被呼为“五呆”,颇有痴呆的景象。林老生于江苏省江浦县江家坂,祖籍安徽省和县人。所以,他的所有活动都与江苏、安徽难舍难分。历史的巧合,沙翁十四岁丧父,林老十五岁失诂……我想,我对林老的生平叙述到此为止的好。因为林昌庚先生的著作为可靠的记录,重复不过来。
这一意外的劫难让他的亲人备受煎熬,林老自己也深受折磨。既然我们在说书学的问题,当然不会停滞在这里不能自拔。即以书法执笔而论,悬腕可以不悬肘,但悬肘必得悬腕。不然,胳膊肘子悬翘起来,而腕部在宣纸上,动作奇怪不说,也难以操作。书家向来讲究中锋运笔,据说何绍基为了达到持续的中锋运行,似乎还要回腕。这个动作很不舒服,回腕回到什么程度,是九十度还是四十五度,则没有准确的记载。后人评论说:“何绍基执笔十分独特,如老猿抱树,回腕高悬,几乎完全违反人的生理自然姿态,但因此而通身力到,极锥沙蚀木之妙。”
何绍基回腕执笔,书法不可避免的在横画里要有弓的趋向。即以行书《论画语》为例,通幅观感看上去如柳絮正旺,飘飘洒洒,尤其撇画,或者还有竖画,从右上向左下飘过去,狼烟四起,却趣味浓厚。林老被烫伤愈后,仍坚持中锋运笔,有双钩之称。但是,仔细观察两幅照片,则并无一定。九十一岁写字照片,双钩无疑,且有回腕动作;《生天成佛》为绝笔,九十二岁照片,则为单钩。林老的晚年书法——即劫难后的书法,通篇并无柳絮的感觉。以拙目观之,行草比何绍基高明。即以舒同论,亦整饬何绍基而开舒体之风。
须知何绍基行草是以颜真卿奠基的,无可否认,林散之亦以颜真卿奠基。那么,颜真卿用笔又从何而来?据沙孟海说,多来自汉隶。如果这个说法大致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小考一下何绍基与林散之的隶书——何绍基的隶书《临衡方碑》;林散之的隶书《临西陕颂》。何书从汉简中得到启示,起笔回锋而收笔一般随它而去,即起笔粗而收笔细。比之原作,已活泼了许多,基本自运了。林散之将《西陕颂》整饬,基本忠实原作无建树。相比之下,隶书不如何绍基。既然说到颜真卿,就不得不说楷书。何绍基楷书《邓君墓志铭》,一派颜体模样而活泼自然;林散之楷书《四友斋论书》是六十年代所作,即碑帖结合的典范之作。收在《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林散之卷》里的书孟浩然《春晓》,则以行书笔意作楷,横画起笔落笔均有回锋,带有汉简的意味,不输给何绍基。
近来学书者,往往不明就里,照葫芦画瓢学模样。有学林散之的,上手就是童稚趣味,须知林老不是故意弄成那个样子的。就生理讲,林老遭难痊愈后,关节活动已经难以灵活,使转——包括绞转吃力。而“草乖使转,几不能成字”。抛却使转,如何作得草书,林老必定要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执笔写字,最忌讳如同鸡啄米刨食状,然则,笔到纸面处呆傻不动,也成问题。但是,林老不能够急速运笔以成风驰电掣状,他得根据他的状况实现他的艺术理念。如果我们不细分的话,将用墨也放入用笔之中,就进一层了。林老用墨据说是浓得很,这浓墨又难以运行,即蘸水调和使之自如。故此,林老的行书或者草书,就有了干擦,有了浓淡的反复无常。如果你想亦步亦趋地学林老,总不至于也烫成五指粘连再开刀分开执笔必要的前三指吧!假如神枪手已眇一目,恰巧左眼,谁也不会为了当神枪手故意弄瞎一只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理特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学术结构,又审美的趣味随着地缘文化的特征而形成,那是要审慎对待的,善待别人很难,善待自己又谈何容易。
用笔不仅仅是执笔。现在执笔无定式已经为广布之说,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林散之最服膺何绍基用笔,据桑作楷先生《沙锥深处悟真诠——论林散之先生书法的用笔》一文,就记录着林老说何绍基:“清代何绍基善用笔,字写得比别人黑,黑就是笔力。”可见,林老学何绍基,并非在字形,而是笔力。林老秉承古代大家之正侧、藏露、强弱、缓急、提按、方圆、收放、虚实、连贯等用笔法之外,根据自身的生理状态,还运用了很多方法。桑作楷先生是受到过林老亲灸的,他总结说林老还有“冲、铺、抛、切、擦、裹、塞、断”等笔法。观林老书法作品,特别是草书,浓淡干湿、俯仰拿捏、虚实出入、疏密布白、急徐运笔,在谨守草书约定俗成的规范的同时,笔到处无不自运而无古人的外形痕迹。林老草书的确有独特的味道,若仅仅论用墨用笔,与康南海相去不远,不过,康南海写的是行书。感官不同处则在于,康南海书法如古木长了些许新芽,而林老则是哗啦啦秋风萧瑟却纸面干净。
收在《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林散之卷》里的《论书绝句十三首》,可视为林老的代表作。即以愚意,观赏草书,最怕笔画多,还怕到处画圆圈。草书本来是简而快,如果草书的笔画比行书还要多,那作品就先输了一筹;牵丝连带固然是草书无可避免的行笔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到处画圆圈,也令人厌烦。诗句“能于同处求不同,唯不求同斯大雄……立德立功各殊途,打破藩篱是丈夫”可视为林老抗心希古的肺腑之言,世人可晓得否!
林老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一直默默无闻,世间并没有几个知道有个叫林散之的人。林老初名林以霖,简化为林霖。自幼喜爱诗词,年轻时即作《古棠三痴生吟稿》,印章即“三痴生”,痴情于书画诗词。在林老的一生中,有三位恩师,初师范培开,再师张栗庵,后师著名书画家黄宾虹。前两位虽未享誉海内,却功底深厚,而黄宾虹则是名副其实的大家了。“林散之”即张栗庵先师取“散木山房之意”谐“三痴”而命名之。我倒觉得,如果林老以“三痴生”用之始终,亦未为不可也。但是,林老“散之左耳”简称散耳,为晚年所用。
然而,这并没有给林带来巨大的名声,一直到公元1972年,林老已经七十五岁,距意外劫难也过去了两年多——意外又来了,为庆祝中日恢复邦交,《人民中国》发表了林散之草书。“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是啊!是林老有意选择这首诗吗?当然是有意选择,但未必是要自鸣。
世间往往就是那样,巧合无处不在。江上草堂——这必然浪漫的名字,又蕴含多少偶然。那颗炸弹落下来,林老在看见那炸弹的时候,还注意到了它的尺寸大小。闭眼等死,炸弹却没有爆炸;洗澡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外又发生了,几乎置之死地;林老出院后,再次被逼回到江上草堂,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了,发表了草书。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灯下黑?这只能看个人的理解了。日本“和尚”带来的不是炸弹,而是“草圣遗法在此翁”,让林散之有了“当代草圣”的美誉。不过,林老十分清醒,认为时名不足取,他说:“评价一个人的艺术成就,要等他死后三百年才能定案。”
林老拖着半残的身躯,将那话放在了时间的天平上,让那些到处找小报记者鼓吹自己是大师巨匠的书家显得轻如鸿毛。时间的天平渐渐失衡,那些当代的大师巨匠们,看上去总有神汉的感觉。真的是大师走了,来了巨匠。
其实,在远来的“和尚”没有来之前,胡小石、因《兰亭序》的真伪跟郭沫若打过笔墨官司的高二适两先生就对林老的书法称赞不已。高二适(公元1903——1977年)诗书俱佳,胡小石(公元1888——1962年),为学者,并非要专门造诣书画。还有一位即女书法家萧嫺,康有为嫡传弟子,书法亦与南海先生相去不远。与林老一起,构成了“金陵四老”之说,求雨山已经一派书法圣地的景象。
非常难得的是,《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林散之卷》有林老的自序。在这套丛书中,这序言就格外珍贵。他的珍贵在于,听听其言,善莫大焉。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书中所选书法作品,是经过林老或者家人过目认可的,保证全是真品而无代笔临仿之虞。
林老浸淫于诗词书画中不能自拔,虽然也曾一度当过江浦县的副县长,那不过是个插曲而已。秉承先代学子的一贯信念,成为学人——无论书画,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始终是不可动摇的,林老亦如是。壮游名山大川,还有《漫游小记》刊诸枣梨。文风可靠,文字简约,内容丰富,美文美事,是不多见的。
我更注意到了林老的变法之说:“变者为形质,不变者为真理……变者生之机,不变者死之途。”书法的“面目各殊,精神亦因之而别。其始有法,而终无法,无法即变也。无法而不离于法,又一变也……颐养之深,酝酿之久,而始成功。”这集成了历代大家的意见而解之,自是森然有序。变法是书法的要务,古今都在想办法。章草书法固然古色古香,有高古的美誉,也保留了隶书特有笔意。很多书家在章草上下了巨大的工夫,然而收效甚微。甚至去掉了古色古香部分,专拣外部特征而发扬,等于是学了圣人的短处。王蘧常对此颇有收获,他的章草就保持了古意而自有面目。王献之不满意章草之法,虽然没有说“未能宏逸”的根本原因,却是有深刻体会的。“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大人宜改体。”如此疑似伪托类的辑录,并不一定真的是王献之所说,但是,离二王的变法以成新的面目相去不远。林老摸索了将近一个世纪,总结出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变在何处,不变处又在于何方。然而,这又不是突兀的事情,“由递变而非突变,突变则败矣”,是为林老最为惊人之语,解者自解,不解者亦无必要与之讨论。
林老一生,即可引陆放翁“老蔓缠松饱霜雪”之句来总结。在现当代对草书有真知的书家并不多,林老是其中那不多中的杰出者。他的草书,在黑白之间腾挪,在坚实与虚空之间挪移,老蔓也好,老松也好,在那霜雪似包裹又难以包裹的状态中,自然转换,显得老辣与冷厉。林老书名大震后,索字者盈门,“如此追偿老命休”——“何处能寻避债台”是林老晚年的自我写照。真不知道这人是出名好还是不出名好,世间追逐名利而不得者,也可以藉此安慰一下吧!公元1989年,12月6日8时,林老在南京鼓楼医院溘然长逝,终年九十二岁。林老最后的日子,从容给儿女们留下“我要走了”那句话,用尽了平生之力写下“生天成佛”已成绝笔。面对一生的论定,连手也不用挥一挥,就走了。那一份从容与恬淡,没有对人生的参透,没有对艺术无怨无悔的深邃理解,是断然难以有那种充分的准备,让很多人为之艳羡。离开人世,不是谁都有从容的机会,不是谁都能够如此的淡定。老人身后竟是那般热闹,购买他的书法集子已经很难,谁又会想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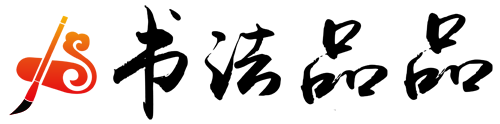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