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富有伸缩性,也即是弹性。行书可分为“行楷”(或日“真行”、“行真”、“楷行”)、“行草”(或日“草行”、“半草行书”)两种。张怀璀《书议》云:“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这里“真行”指“行楷”。而对于王献之首创行草的特点,张怀璀总结得最为详细:“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变。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
这里对两种书体进行比较,尤其赞赏行草为“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说明行草的杂糅性,具有审美的多元性;同时对二王父子的书艺成就作了比较,指出了两人各自的长处,对六朝以来父子“孰优孰劣”问题进行了澄清,从此后书评中再无异议。姜夔是南宋书论中著名的“风神论”倡导者,他认为,行书应“大要以笔老为贵,少有失误,亦可辉映。所贵乎裱纤间出,血脉相连,筋骨老健,风神洒落,姿态备具,真有真之态度,行有行之态度,草有草之态度。必须博学,可以兼通。”这里将行书比喻为一位成熟稳健的人,姿态多样而体现出洒落的风神,在乎博学兼通。当然,宋人受理学家“积学为功”思想的影响,对“天姿神纵”的天才论虽然不反对,但更强调后天的学习,读书明理,格物明理,贵在“尽其性而知其天”。明代项穆云:“不真不草,行书出焉。似真而兼乎草者,行真也;似草而兼乎真者,行草也。”与张怀璀所言意同而说法易让人误解。刘熙载认为:“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纵于真,草行近草而敛于草。东坡谓‘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行岂可同诸立与走乎?”他又明确提出:“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知真、草之于行,如绘事欲作碧绿,只须会合青黄,无庸别设碧绿料也。”可见,行楷是楷书的简捷和流动形态,行草则是草书的周详和安静形态。只要学好楷、草,适当加以变化则能得行书之要领。无论行楷或行草,行书都是文人书法最为注重的书体,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行书可以表现韵趣,以体现不俗之人格为尚,超越技巧为高;第二,行书以适意为主,不要太受法度之限制,故有乐趣;第三,行书可以脱略行迹,偶有败笔亦可,整体要协调;第四,行书变化多端,有“定理无定势”,新意妙理常见。第五,在行书中“行气”(或称“书脉”)更为重要。
行书的魅力关乎人格的超拔。刘熙载评米书:“米元章书脱落凡问,虽时有谐气,而谐不伤雅,故高流鲜或訾之。”这“谐气”指戏谑的意味或习气,有经漫之气。但小疵不伤大雅,更见性情。行书是“雅逸”之风度、神韵、气质之再现,自然不能仅仅要求点画之笔笔工稳,而重在“势”、“气”的连贯,体现出生命色彩。所以,刘熙载在《书概》中的格言“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一语最为警拔。因为行书最能看出书家的情性和审美趣味,其韵律和节奏最能表现书家生命的真实。六朝时期,品藻之风盛行,论书与论人相结合。论人包括人之外貌、气色、气质、神采、才情等,都可以在书法的点画形态中去观察。如宋人论陶弘景行书:梁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身长七尺四寸,神采耸秀,有仙风道骨。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而行书尤妙。大率以钟王为法,骼力不至而逸气有余。然苦心笃志,未尝懈倦。
这里涉及“帖”与“碑”的关系问题。“帖”最初是指纸本或绢本上的字迹,如行草手札、尺牍,是以非正规书体(篆、隶、楷之外)的行草为主的书写形式,用于私人之间的交流和问候等。阮元先生认为:“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帖为简札之类,这是可以肯定的。但在刻帖的时期又能转化为法帖,也可刻入碑林成拓片,成为“碑”的形制。在体积上是应以小巧玲珑为主。有人认为《集王圣教序》刻石,是集王羲之简札而成,应仍称之为帖,不可称之为碑。这里,是以字体分类,常常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模糊性。
而与此有关的“帖学”,一是指研究考订法帖的源流、优劣、真伪、拓本之先后及文字内容的学科。二是指宗尚法帖之书派,与“碑学”相对称。一般又称南派。一般认为,帖与行、草的关系较为密切。阮元《南北书派论》认为:“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北碑南帖论》日:“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虽然对南北分派历来意见不同,但对“帖”与“碑”的特点作出了相当的界定。郑孝胥认为:“南朝土人雅尚清谈,挥麈风流,形诸简札,此帖学之萌芽也。唐太宗好《兰亭》,于是有唐一代书家,无不学王者。苏灵芝欲展《兰亭》为碑,此以帖入碑之始。其书实伤婉丽,所谓俗书之祖也。”看来碑与帖有各自的特点,不能混为一谈。
许多书家能写小手札,而无法写大碑巨碣,失之气魄和骨力,也有许多书家大书深刻而小字不佳,失之韵味和意趣,都是没能兼通之故。相对而言,碑帖相济是比较难的。
声明:本站文章、图片、内容仅供个人学习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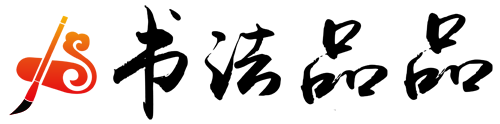
评论(0)